阿拉伯營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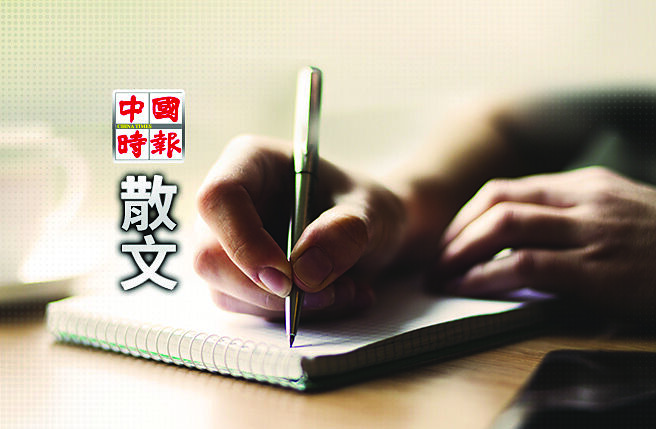
散文
那年的春天,我登上了新兵專列,火車緩緩駛離臺北,心中涌起一股難以言喻的失落感。大學聯招的落榜,意味着我的夢想被迫擱淺。車窗外的臺北景色逐漸遠去,心裡既惆悵又不安,彷彿一切都隨着這列火車駛向未知的命運。
來到了臺中的車籠埔新兵訓練中心,開始了爲期三個月的新兵訓練。每天清晨,我們在急促的哨聲中醒來,立刻整理內務,疊好棉被,所有動作必須精確迅速,因爲稍有拖延便會受到處罰。在炎熱的太陽下出操,汗如雨下,肌肉痠痛無比。我們吃的米飯是戰備存糧的陳米,裡面經常有米蟲。儘管操練辛苦,還是得咬牙堅持下去。
當時訓練中心的一位營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隨國軍從大陸撤退來臺的回族人,輪廓深邃,膚色較深,讓人聯想到遙遠的中亞或中東地區。我們爲他取了「阿拉伯營長」這個外號,但未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因爲他的氣質與領導能力讓人感到敬佩。
「阿拉伯營長」的兵種是騎兵,這在臺灣陸軍中相當罕見。在1970年代,騎兵這個古老的兵種早已在許多現代化軍隊中逐漸消失,但他仍然是這支兵種的少數傳承者。他年輕時接受過騎兵訓練,並且曾經參與過國共內戰,戰爭期間帶領馬匹奔波於戰場。
營長對我們非常嚴格,尤其是對紀律和訓練的要求。他的眼神銳利,任何細節都不會放過,總是面帶威嚴,他是那種會讓你立刻感到他的存在感的領袖,不需多言,僅僅是一個眼神或一個動作,便能讓全營的士兵立刻挺直腰桿,打起精神。
訓練時,營長可能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他強調操練中的高度專注,稍有疏忽便會被立刻糾正。他經常告誡我們:「現在對自己嚴格,戰場上才能保護自己和戰友。」
有一次在野外訓練,學習攜槍跑步,臥倒。他認爲教導的教育班長動作不夠俐落,當場親自示範。他提起M1步槍,低姿快跑,自己下令:「臥倒!」只見他左手肘迅速着地,全身貼着地面,靈活匍匐前進,接着一個翻身蹲起,手中的步槍瞄準前方。他起身時,原本整齊的軍服已滿是塵土。營長的教導,讓大家口服心服,無不敬佩。
射擊訓練時,成績不好的新兵會加強訓練。他會帶領着連長一起上陣,從握槍姿勢到扣下扳機的細節,一步一步示範指導,而營長的百公尺射擊幾乎百發百中,他驕傲說自己年少時在馬背上學習射擊,練就一手好槍法。
某些時候他又像一位嚴父般照顧着我們,晚點名後大家準備就寢前,他會偶爾來探望,與我們這些想家的新兵聊聊。他難得地和我們談起了家鄉的點滴,提到小時候在北方草原上騎馬的日子,還有家裡的清真寺以及家族裡的習俗。他的話語間,保持着軍官的冷靜,但我們能感受到流露出的淡淡鄉愁。這一刻,我們不再覺得他是嚴苛長官,而是一位真情流露的鐵血軍官。
訓練接近尾聲,我們將告別新訓中心,展開軍旅生涯。那一年,蔣中正總統逝世,全國上下陷入一片肅穆,政府則爲即將到來的國慶大閱兵緊鑼密鼓地準備,以振奮人心。大部分結訓的新兵被分派到新竹的預備師,參與閱兵踢正步訓練。
營長親自來爲我們送行,他的嚴峻眼神一如往昔,卻帶着無法掩飾的情感,我們能感受到那一絲深藏的牽掛與不捨。那一刻,我明白,「阿拉伯營長」的身影將永遠刻在我記憶深處。
他的故事不僅屬於他個人,更是那個時代無數軍人的縮影。他們揹負着家國的歷史記憶,默默奉獻,不辭辛勞地鍛造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新兵,無怨無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