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緒,《我的詩學筆記》選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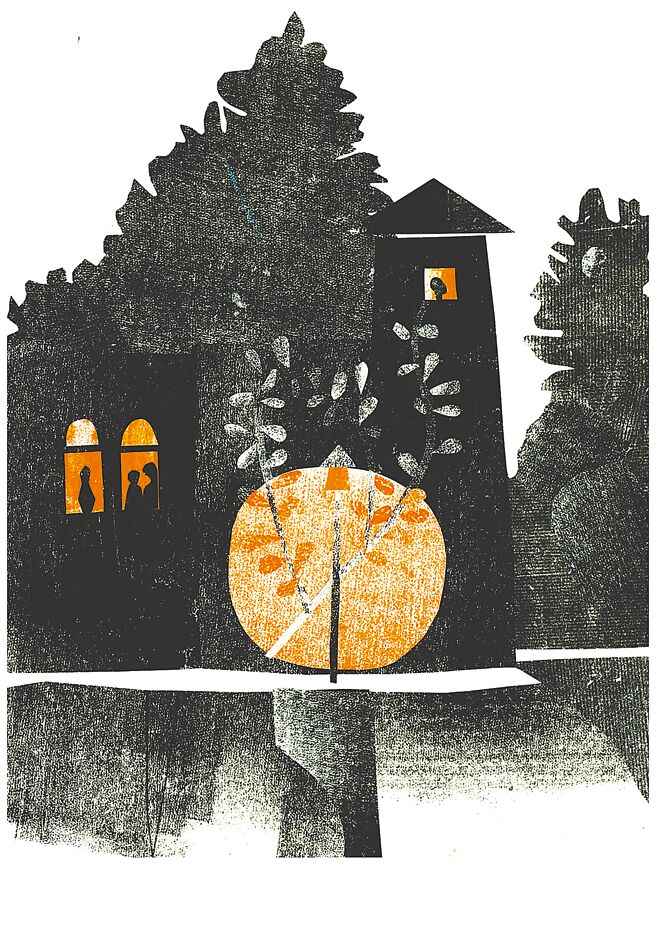
神秘夜色⊙圖/李宛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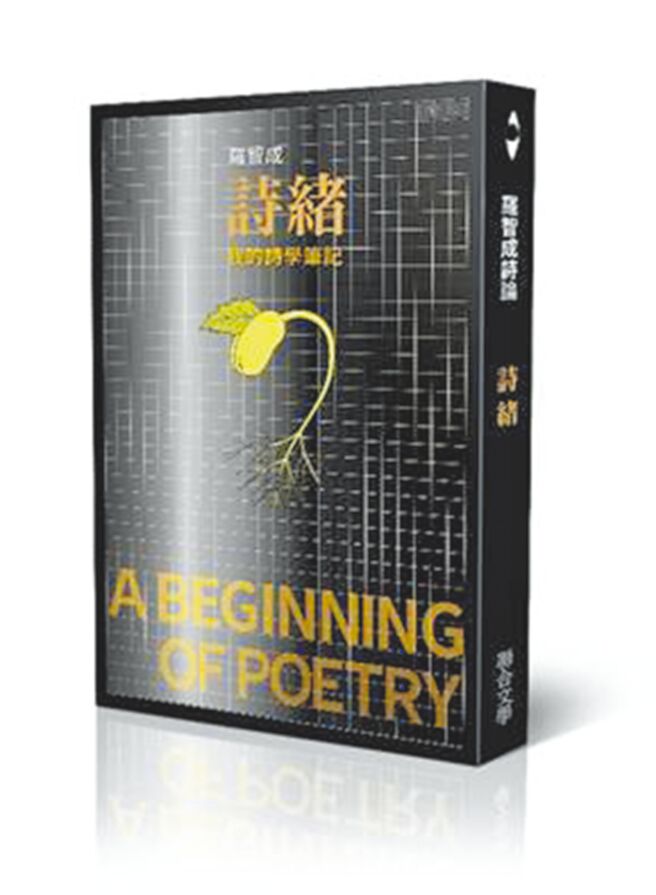
《羅智成詩論--詩緒:我的詩學筆記》,聯合文學出版。(聯合文學提供)
2.3.1
但是我們仍必須去嘗試、去說出,
作爲跟自己、跟別人溝通的途徑
作爲階段性的經驗與思考的整理
作爲某種理想文學創作的出發點
也爲下一階段的探索奠定更具體、紮實的理念基礎
2.6
但是,關於詩的思索與想像
不完全是創作之外的後設描述、銓釋與觀察
它本身,就是與詩創作同步的心智活動
關於詩的思索與想像
其實在創作的當下也是時時刻刻在發生
5.5
詩質不太會是附屬於特定物件上的品質,
因爲詩作爲一個概念,本身就是抽象的存在。
我會試圖這樣描述,所謂「詩質」
通常是指:
被情感、修辭、創意、個性、態度,或者說,
被特定的態度
提煉過的語言所呈現的氛圍(或某種刺激),
這樣的氛圍會
強烈、廣泛、快速地在讀者的內心產生美感經驗、豐富暗示
以及情感與思維上的連鎖反應。
5.6
精練如何發生?
我們於是來到詩概念形成的下一個階段:
詩如何藉由多方面的精煉與提升得到了它的「質」?
5.8.3
在中文世界,文字的精練更受重視,
原因在前已約略提及。
詩歌特有的儀式性、社交性與專業性
獲得識字的菁英階級高度認同與重視,
「不學詩,無以言」
特定階級的作者與讀者共享着
精深、優美的溝通與社交文化,
拉高了詩文學的語境,拉高了創作與閱讀的門檻
而幾個世紀以後,
隋唐的科舉制度把語文能力視同心智與管理能力
讓詞章優美的才華之士得以成就功名利祿
讓詩的精進在中國有了更強大的社會動能
也讓詩藝成爲展現才華的最高舞臺
與此同時,我也一直認爲,
詩之所以具備現在我們所熟知的這些特質,
還有心理與物理上的必然
6.5
無數學者討論過,
「現代」,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有些人溯及文藝復興時代、啓蒙主義時代或者是
一七六O年代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那一次的劇變主要源於蒸汽機的發明,
各式燃煤機器開始代替人力與獸力工作,
改了生產的方式與效率。
也有學者主張一八七O年是個好年分,
因爲那一年並沒有特別的重大事件發生,
不致讓人誤解是某單一關鍵因素導致「現代」突然誕生。
但是他還是忍不住地提及那一年的普法戰爭──
在那之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歐洲本土基本上已沒有戰亂,
全力衝刺於生活、科技與產業的發展,
這段時間是有史以來文明進步最快的時期。
也疊合史家所謂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也有一些人把「現代主義」限縮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也許是更着重於強調現代主義晦澀、疏離與荒謬的特徵,
或對存在情境與本質的覺醒與探索,以及戰爭對於文明、
對於人類心靈的傷害與衝擊。
當然,我們的視野僅能涵蓋一些當時先進地區,
因爲整個地球並不是同步進入現代的
6.9
在我還不清楚波特萊爾和愛倫坡的密切關係之前的年輕時期,我同樣的,也被愛倫坡零散卻令人着迷的各種作品深深吸引。對這個當時文學主流的邊緣人在現代文學所貢獻的靈感與深遠影響感到極大的好奇。
我特別喜歡〈大鴉〉這首詩,因爲它有着死神般的黑暗力量
在歌謠般的復沓中,某種呼之欲出的不祥預言
一次又一次加重着生命的陰影與愛情的狂亂
宛如一個通靈的詩人試圖揭露噩運之謎
卻飽受烏鴉冷然駁斥,益顯無謂、徒然
讓我們對受苦靈魂的命運更覺悚然……
愛倫坡的詩作不多,包括輓歌般的〈安納貝爾‧李〉
召靈曲般的〈鐘聲〉或〈烏拉露姆〉
風格和主題始終維持着神秘的死亡與迷人的陰鬱
透過他,我才進一步認識了哥特派的風格
而他作爲創作重點的衆多懸疑小說特別令人耽溺
愛倫坡短篇故事引人之處不僅來自他的情節、構想、佈局
抽絲剝繭的分析或現買現賣的科普新知
更源於那陰鷙不祥、有着濃厚悲劇性格的感染力
像一個苦心孤詣的幽靈
在一個密閉、沒有出口的結界裡上下求索
他的肉體已經衰敗、腐朽,甚至已經沒有實體
只剩各種靈敏、清晰、令人隱隱作痛的官能記憶
這些黑暗的全境式感官氛圍是由具有高度同質性、
象徵性的景物、建築、空間、人物與怪誕言行組成
屬於全人類的幽暗意識
特別易於傳播、感染
在我們時刻提防的惡夢裡作祟
就這一點而言,
愛倫坡可能比之前任何一個哥特派風格的作家
更接近他們下意識追求的終極哥特派風格
他的心理背景、駭人想像與濃重的官能刺激
更是當今各式媒體中哥特美學的原型
6.10.2
我還可以十分肯定地宣示
在二十一世紀的此時此刻
同樣的,更多、更巨大的科技躍進
各式硬體、軟體快速的質變與量變
文明史上新一波的感官主體的改變正在發生
而且遠比以往的更激烈、更徹底,一直
動搖到我們自我認知裡的「人類性」
8.3.3
詩的創作直接或間接的都是爲創作者思考、建構出一種理想
的關係,他與文字之間的關係、他與讀者之間的關係、他與
世界以及他與自己的關係。這些關係來自於渴望、來自於觀
察與反省。詩人內在最大的焦慮,就是在這個並不是爲他量
身打造的世界,爲自己的聲音找出一個量身打造的位置。
(本文摘自《羅智成詩論--詩緒:我詩學筆記》,聯合文學出版)













